永远葆有书写的热枕
发布日期:2024-12-23 作者: 文章来源:大洋网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前几天收到镜明兄赠阅的新书《我心安处是丽江》,读罢放下,沉寂了十多天后,今天终于有感而发。
就我个人感受,新冠的最大后遗症就是我变得“懒语”了:能不说的话,尽量不说;能用嘴说的,就不动笔。懒语当然还不至于“失语”,主要是文字表达的冲动日渐淡了,笔头也像锈蚀了一样,就算写个短短的朋友圈文,也变得磕磕绊绊。究其原因,有后现代碎片化文化特征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我内心对“书写”在当下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动摇:既然人生都是虚妄的,用文字去记录个体存在的痕迹,又有什么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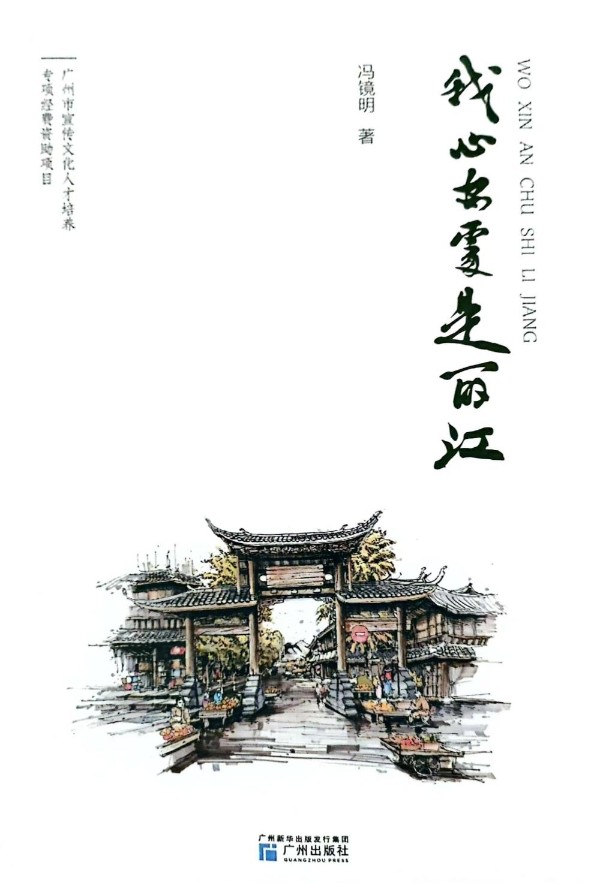
当我捧读镜明兄这本新书,字里行间,却无处不透露出他对文字表达的热忱。他娴熟精准、徐疾有致地书写着他对丽江的历史、文化、人和物的热爱,笔下的文字仿佛也如纳西古乐般生出了旋律,文字之美又远胜于他十年前的那本《我与世界相遇》,这甚至让我颇为惊诧。我当面询问过他何以如此执着于书写,他给予我这样的回答:“唯有文字,庄严地宣告生命曾经存在。”颇有几分古人要藉着文字留名青史的味道。这样的回答虽不至于让我醍醐贯顶,嘴里依然在讥讽他迂腐食古,但内心却着实钦佩他对书写意义的坚守,一个人能在历经风霜后依然葆有对书写的极高热忱,这种品质该有多么的难能可贵!也意识到在他眼里,我自己对书写意义的解构和挣扎,该是多么的负面和不可取。
一个人的写作方式和态度,当然与他的人生和工作经历有关。镜明兄从暨大新闻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每天都和文字打交道。2000年前后,那时的我还是某日报政文部的一名新兵,他已经是“贵”为某部门主任了(这也是我现在总是称呼他“领导”的原因)。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惯常会看到采访回来的他,边跟几个部门主任热络地打着招呼,边旋风般从我的卡位旁走过,留下一串洪亮的声音和一个英挺的背影。当下,我是无论如何难以将他与眼前的文字联系到一起的。人是如此外向、活力四射,隽永的文字却一如盘绕丽江古镇的溪水,又如玉龙雪山上的蓝天,充满想象的空间。
也许这一切仅仅就是时光的馈赠。大概两年前的某次朋友聚会,我发现“领导”餐后从随身带的一个布袋里面掏出了四五个瓶瓶罐罐,一问竟然都是自国外进口的营养补剂。他向我们如数家珍般讲解着各种补剂的功能,也劝我们要及时进补。我本以为他难以坚持,没承想每次聚餐,他都会拎着那个旧旧的布袋子,准时地在餐后半小时内让这些五颜六色的补剂进入腹中。毫无例外的,每次他的这些行为都会成为朋友们揶揄的谈资,他却毫不为意,执拗地讲述着这些补剂如何滋养了他的身体,也让他更有精力从事写作。
我嘴上虽然不说,内心却不得不承认,年届花甲的他,看起来还像个四十出头的青壮年,也许真的与坚持吃那些补剂有关。纵然这样,我还是感到眼前这个每天拎着个装着各种补剂布袋子、满口养生之道的“领导”,同二十多年前那个充满阳光活力的青年才俊形象反差有点大。若果形容他之前是动若脱兔,现在就是静若处子的状态。这状态也许让他的文笔少了辛辣,但在静谧无声中却平添了优美和深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丽江。去过的,没去过的,大致都会首先把丽江视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然而,《我心安处是丽江》这本书却不是。读这本书时,凭直觉就能触摸到作者对丽江的热爱在字里行间流淌,就像听一个当地的丽江人在给你讲述着丽江的前世今生以及她的各种好。请放心,这本书中绝没有游客视角的平铺直叙,当然也不能作为丽江旅游攻略。你将读到的、共鸣到的,只是一位永远年轻的新闻人不务正业的“美文”,他用每一个珠玑文字,书写着他对丽江的热爱,也在彰显着书写的意义。
编辑:阿尺